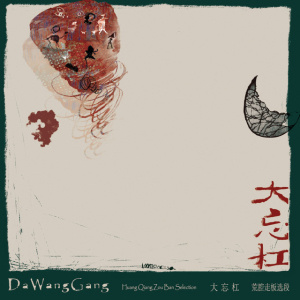
荒腔走板
荒腔走板的现代变奏
“摇滚之外,另一个宋雨喆在路上。一个渴望修行者去西藏,但他深知苦修的无望,正如生命的无望,摇滚的虚妄,或许他会回来,绕无数的弯回来……期待着一个新的宋雨喆,一个新的木推瓜。但假如有一天他也混在《格萨尔王》的游吟行列中,成为一名无名的游吟者,化作大地上的一阵大风…… ”这是年我写的评论木推瓜乐队的文章《被烈火释放的囚徒》,当时木推瓜已基本解体,所以我给文章加上一个煽情的尾巴。
现在这个尾巴被大忘杠重新点燃,但大忘杠并不是一个新的木推瓜,宋雨哲告别木推瓜很大程度上就是告别摇滚乐,给被愤怒和绝望弹断的神经重新接上一根放松的琴弦。他确实消失了好几年,当剑拔弩张的自我最后只剩下自相残杀,这个摇滚逆子只能将自我消弭于宗教之中,并学习如何在大地与民歌之间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他并没有皈依,他最终还是回来了。
游牧民族民间音乐和诗歌,宗教,大地山河,构成大忘杠的强大磁场,然而宋雨哲并不被任何一块磁石吸走:既不是某一民族音乐的传承也不是某一宗教的传神,既不是异域情调也不是乡愁味精,既不是民谣也不是摇滚,既不是民族音乐也不是world music,大忘杠的挑战在于:荒腔走板如何现代变奏。
所谓荒腔走板所涉及的无非藏蒙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游牧民族。大忘杠音乐上再天马行空还是有基本的准则:不翻唱翻玩任何民歌民谣,不依循任何民族音乐老套——有些旋律动机有民歌韵味,但节奏和调性则刻意求新,配器更是有意“离谱”:宋雨哲早已不用吉他,近年他演出最喜欢的乐器是班卓玲,但班卓玲现在多用于其个人民谣,在大忘杠中有意弃用,而一一操弄诗琴,曼达琴,八弦班卓琴——基本上是跟藏,蒙,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没什么关系的乐器。而马头琴和艾捷克这样的游牧民族标签式传统乐器,在大忘杠中则被尽量撕掉标签玩出新意。有一次演出,宋雨哲要胡格吉乐图先拉一个马头琴开头,但胡一拉宋就叫停:“太蒙古了,再往东一点!”
不要光被民族音乐的磁场吸进去,进得去更要出得来。
《山道上撞见两个咒师》和《说鸟二》是整张唱片最能体现乐队风格水准和未来方向的“大歌”,马头琴加艾捷克的配置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两把弦乐在《咒师》中渲染出的醉酒头痛般的诡异氛围,在《说鸟二》中则是一阵阵像是骑兵拦腰冲破方阵的节奏狂欢。诗琴加上艾捷克马头琴,小打击乐再加些采样,这就是大忘杠最齐全的配置,也是现场阵容。《说鸟二》是唯一能接上木推瓜血脉的歌:如履薄冰如临悬崖,失足的节奏惊险万状,戏剧化的唱腔——当年标志性的假声高腔再次像幕布一样卷起,杀千刀的肉嗓再次杀出一条血路。
《四条道》和《猎人》则是八弦班卓主导的极品民谣,配以马头琴和口弦,小打击乐。过耳不忘的旋律,堪称宋雨哲迄今最为通俗最宜传唱的歌;致小儿》和《林卡里的瘦熊》属于可简可繁的歌,介乎小调与大曲之间,这次做的是简化版,《林卡里的瘦熊》省略了纵情的肉身和鼓点,只留下诗琴和曼达琴像飞天的两条衣袖任人挥洒想象。
两首纯曲子《解放无人区》和《狮子麻扎》在专辑中有些突兀,与其说是玩实验,还不如说是营造秘境,大大拓展整张唱片的空间感,也体现了宋雨哲喜欢的制作思路:将野外录音与室内录音相结合,《解放无人区》中还加进李铁桥在地下停车场奇特声场中的萨克斯。《狮子麻扎》是专辑中易被忽略的作品,但却很能体现宋的创作套路:所谓“麻扎”即是墓地,“狮子”指的是10世纪的阿尔斯兰可汗,在喀什的“狮子麻扎”俗称奥当麻扎,宋雨哲采样了狮子麻扎守灵人的歌,但做出的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萨满或伊斯兰祭祀音乐——而是以口弦和半筝做出巫气深重霸气十足的音乐,要的就是传说中的“神似”。
宋雨哲的歌词源于民歌和民间文学中的动物寓言传统,他和小河几年前曾致力于收集和改写民歌歌词,但大多不是照搬而是再创造,《说鸟二》改写了一首西藏民歌,而《猎人》的诗意多少受到仓央嘉措的启发,仓央嘉措诗曰:"去年种下的幼苗,今岁已成禾束,青年老后的体躯,比南方的弓还弯"。宋雨哲则青出于蓝:"娃娃们像山里的野葱,头扎在泥里藏着,妈妈是家门口弯着腰的树,下半身埋在土里等着。"
"狼嚎月亮是感动,鹰抖翅膀是放松"(《致小儿》),两个常见的意境令“感动”和“放松”这两个词变得新鲜,宋雨哲对词语一如对音色一样敏感,像《四条道》本身就是漂亮的小诗,他也善用拟声词增加血气和泥土气息,避免过于文雅修饰。
荒腔走板系列中,西藏和藏区占去很大分量,喜马拉雅主题和安多主题不断回响,作为一个曾差点皈依的人,宋雨哲企图在人与神之间还原西藏的活力,或者说通过西藏发现人与神和平共处的奥秘:那些被郑钧的西藏小资情调,陈丹青的西藏人文情调和吕楠的西藏宗教情调遗忘的西藏真性情,比如《说鸟二》式的幽默讽刺,本来就是藏族民谣一大传统(不妨参见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中采集记录的不少街头政治讽刺民谣)。如果说《山道上碰见两个咒师》阴郁神秘,渲染了俗世艰险,那么《林卡里的瘦熊》就是从神那里重新解放肉身——刻板的殉道苦难叙事遭到了质疑,宋雨哲写出四句经典真言:“鱼儿尊敬海子,还在里面拉屎,花儿尊敬太阳,还敢与它对视。”在其个人民谣《到海里应该游泳》中甚至有更直接更貌似渎神的:“供奉女神要露出鸡巴,这样心才无挂碍。”而在送给小河的那首《去边境》中也有如此觉悟:“找准自己的神,摸着它的脾气它就爱你。”
荒腔走板三部曲包含《三个空行母在商量》,《阿西克城》,《曼陀罗上曼陀铃》三张唱片,这只是一个选集,主题和风格难免跳跃过大,令人抓不住头绪,从喜马拉雅到天山,从小调到大曲,从民歌采风到噪音萨克斯风......并且显然因为没钱,其录制缺憾难免,比方说《说鸟二》中人声的极致张力不够,《狮子麻扎》的口弦音轨不够繁密浩大,但当年在木推瓜没能出版唱片的宋雨哲总算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而且无疑是一张经典唱片。大忘杠如同木推瓜一样难以定义,如果不贴标签就得死翘翘,那只能说木推瓜是前卫摇滚,而大忘杠是前卫世界音乐——这真的是一个迫不得已的world music标签,它混淆模糊了民族音乐,你能感觉到民族音乐的某些气息和意境,但无从发现民族音乐的具体标签;它用了一点胡天胡地的前卫手法,但又扎根于民间——胡乐原本就属于胡天胡地,这样的荒腔走板是对雅乐正统的当头一棒,对伪前卫假民族的当头一棒。
不管是对于民族音乐,还是对宗教文化,大忘杠好就好在都只是若即若离,途中相遇,没有盟誓和皈依,只有告别和出发。
价格/ ¥100.00元
立即购买